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2025年9月15日至9月19日,英国皇家学会会士、皇家历史学会理事、华威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奈茨(Mark Knights)专程来访,为我院同学讲授“近代早期史专题课程”。该系列课程共四讲,包括三场讲座和一场工作坊,由历史学院赵涵老师和卿倩文老师主持。该课程不仅吸引了我院世界史试验班、历史学基地班、强基班的诸多本科生选修,还吸引了校内外其他专业的学生旁听。

9月15日
第一讲题为“腐败横行?——近代早期英国与欧洲的卖官鬻爵和贪赃枉法”(Corrup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ow Corrupt was Britain?)。奈茨教授首先梳理了“腐败”概念的多重含义和历史演变。他将腐败划分为四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即官员因贪欲或私利而堕落;二是政治决策受到经济利益的不当影响;三是制度性腐败,18世纪一批思想家认为,制度本身才是腐败的根源,因此呼吁进行全面改革;四是系统性腐败,即整个社会或文化体系的腐败。
奈茨接着分析了近代早期欧洲的腐败现象,重点探讨了1600年至1850年间英国的腐败问题和在反腐败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他指出,彼时法国和西班牙普遍存在卖官鬻爵现象,官职不仅是一种公共职务,也是一种能被交易的私有财产。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佛罗伦萨、德意志、荷兰和英国等地。在17世纪,英国官职私有现象严重,许多职位通过荫庇关系或金钱购买获得。然而,这类做法逐渐受到议会、枢密院和公众舆论的限制。腐败问题还蔓延到加勒比和印度殖民地,在财政压力和社会舆论的作用下,英国陆续推行了一系列反腐措施,官职逐渐由私人财产转变为公共信托,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分离,买卖官职也被法律明确禁止。
奈茨教授总结道,腐败与反腐败是理解近代早期英国及欧洲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腐败既存在于个人和制度层面,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研究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不能简单套用当代标准,而应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其涵义。讲座最后,奈茨教授邀请在场听众共同评判17世纪英国的海军部官员萨缪尔·皮普斯是否腐败,随后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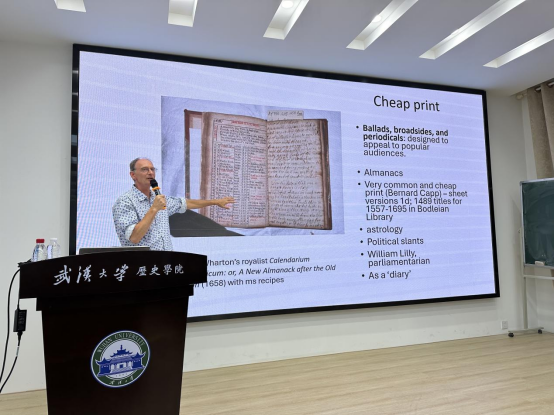
9月16日
在“腐败与反腐败:近代早期英国的法律、丑闻、殖民帝国和政治文化”工作坊中,奈茨教授进一步从“信任”(trust)、丑闻以及帝国治理三个角度阐述英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历史。自17世纪起,“信任”逐渐成为政治权威的重要基础。国王、议会与官员被视为承担公共“信任”的受托人,一旦背弃这种信托,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信任”逐渐制度化,推动了监督与问责机制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建立。
在谈及丑闻的政治功能时,奈茨教授指出,随着印刷品的发展,腐败丑闻可以煽动公众情绪,公众扮演了“陪审团”的角色,对违背信任的官员进行批判。但借丑闻抨击腐败,难以触及深层的制度问题。奈茨教授还主张将腐败置于更广阔的帝国范围内进行考察。沃伦·黑斯廷斯弹劾案表明,腐败既关乎个人声誉,也与帝国统治息息相关。最后,奈茨教授强调,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缓慢、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17至19世纪的英国,正是在无数腐败丑闻、逐步推进的制度改革以及持续积累的政治经验中,才逐渐建立起一个相对清廉的政府。
讲座结束后,来自中山大学的李诚老师、清华大学的张烨凯老师、武汉大学的蒋焰老师和卿倩文老师与奈茨教授进行了对谈。卿倩文围绕问责与信任,追问公共制度改革与公众观念转变进展缓慢的原因。张烨凯以海军官员萨缪尔·皮普斯为例,探讨了应如何评价私德有亏有亏但公共贡献突出的人。李诚就奈茨教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强调了将原住民视角纳入殖民史研究的意义。蒋焰老师则对印刷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17世纪对信任概念的强调以及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和局限等方面提出了疑问。
奈茨教授逐一回应。他指出,研究腐败不应局限于单一学科,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恰恰来自历史学之外。他称历史学者有时像“偷蛋的喜鹊”,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思想养分,从而拓展研究视野。他提到法律演变具有“棘轮效应”,每一项司法判决都在不断调整公与私的边界。在殖民地史料方面,他以东印度公司保存的大量波斯语文献译本为例,指出我们可从中捕捉原住民的声音。关于印刷文化,他强调腐败指控常随政治事件传播,当法律途径失效时,媒体也是揭露腐败的重要工具。

9月17日
第二讲题为“印刷品如何改变世界?——近代早期英国与欧洲的印刷文化”(Early Modern Print Cultures: How Revolutionary was Print in Britain and Europe?)。本次讲座回顾了自15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以来,印刷文化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演进,深入探讨了它在宗教改革、政治斗争、社会交流和文化传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奈茨教授首先探讨了欧洲“印刷革命”的内涵和意义。活字印刷术的推广使书籍与图像得以大规模复制,不仅推动了知识的广泛传播,也为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提供了条件。在宗教领域,印刷品成为不同教派展开辩论的工具。新教徒借助小册子、宽幅民谣和讽刺漫画抨击天主教会的腐败,天主教徒也利用廉价印刷品进行反击。廉价印刷品的流行说明,印刷文化并不局限于精英阶层。传播迅速、价格低廉的小册子,常用于政治动员或宗教宣传。朗朗上口、便于传唱的宽幅民谣,提供节气与生活指南的历书,以及自18世纪逐渐兴起的报纸和期刊,它们最终成为传播消息和观点的主要媒介。
印刷品拓宽了人们的阅读范围,也使民众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的讨论中,印刷文化与政治文化逐渐发生联系。小册子、讽刺漫画等廉价印刷品在揭露官员不当行为方面影响显著,但它们将问题归咎于个人过失的倾向,掩盖了机构和制度上存在的问题。随着报纸在17世纪的兴起,新闻传播更加迅速,咖啡馆、沙龙等新型社交空间则为阅读和讨论提供了重要场所,构成了“公共领域”的雏形。英国政府对印刷品制定了一系列审查制度,1695年出版许可制度的正式废除,终使英国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出版自由。但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即便在18世纪,英国政府依然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对出版物施加影响。奈茨教授最后指出,印刷文化并未取代口头和手写文化,而是与它们长期共存、互相补充,交织成近代欧洲多元的信息传播网。在提问环节,奈茨教授就廉价印刷品的流通过程及其人民性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9月19日
第三讲题为“人民的声音如何被听见?——近代早期英国和欧洲的大众政治与请愿”(Popular Politics and Petitioning: How was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heard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Europe?),探讨了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政治的形态,重点分析了请愿活动及其相关形式在英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奈茨教授首先对“大众政治”进行了界定,他将其理解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持续进行的协商过程。在近代欧洲,尤其是在英国,请愿是一种常见的政治参与方式。它既可由个人提出,也可由集体联署发起,内容既涉及日常纠纷(如邻里矛盾或土地争议),也可上升至宗教、税收、政治等重大议题。请愿具有双重性,它是非对抗性的沟通手段,但也可能演变为政治冲突的导火索。奈茨教授向同学们展示了手写请愿书和印刷请愿书的区别,他指出,印刷术的普及使请愿不再局限于本地纠纷,而是关注更广泛的政治与社会事件,引发更广泛的群众参与。例如,一份请愿可能招致反对者的“反请愿”,形成公开辩论,这种情况在17世纪后期尤为常见。
“署名共同体”是讲座的另一个重点。联名致函、宣言和政治结社,都是民众表达集体立场的一种方式。奈茨教授展示了一份1696年英国诺里奇市民的联署文件,在这份长达10米的联署文件上,有该市几乎所有成年男性的签名。奈茨教授还比较了不同文化的请愿传统。例如在中国,请愿语言往往谦卑委婉,但仍强调官府负有回应的责任。而英国在17世纪后期出现了将请愿视为“自然权利”的观念,请愿的措辞更加明确和坚定。
在对谈环节,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和文凯教授与奈茨进行了交流。和文凯指出,请愿不仅是表达诉求的方式,也是对权威合法性的认可,政府的应对方式则会影响其合法性。他区分了两类请愿:一类涉及减税、救灾等具体需求;另一类则涉及宪法权利和国家治理。后者在英国尤为突出,它甚至推动了制度变革,这在中国社会中则较为少见。奈茨教授补充道,尽管请愿通常被视为低风险的行为,但一旦触及统治原则或主权问题,仍可能招致严厉的惩罚。

腐败与反腐败、印刷文化以及民众请愿这些主题相互关联,是理解近代早期英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方面。本次课程不仅拓展了学生对相关史实的认识,也在方法与视角上带来了启发。马克·奈茨教授对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和思考表示高度赞赏,同学们则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了奈茨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系列讲座活动在热烈而真诚的氛围中落下帷幕,与会师生都表示受益匪浅。
(李蕊 撰写 谢美泓伊 摄影 )



